作者:王熙恩
【核心提示】强制阐释而来的意义似是而非,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征用文学证明自身,背离文本原生话语的意义指涉,这是强制阐释的核心性质,势必会侵蚀、破坏文学理论的本体,使之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当代文论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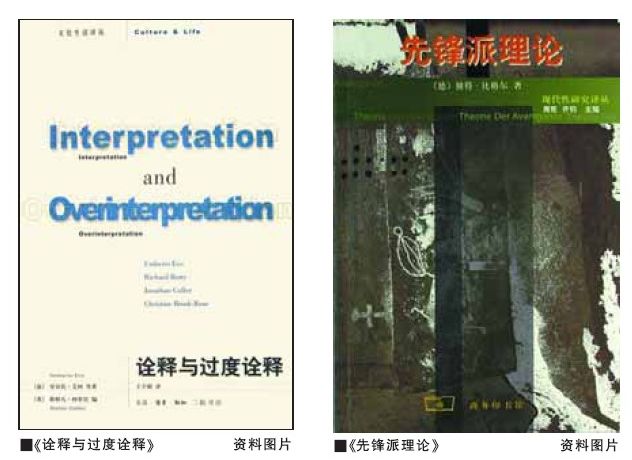
在对当代文论的反思中,艾柯等人提出过度诠释的概念,用以描述文学释义中背离作者原意的“无效阅读”;张江提出强制阐释的概念,用以描述当代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两个概念看上去相近,但在性质、特征和批判力度上却有很大的分野。后者不仅揭示了当代文论的危机根源,而且对当代西方反启蒙、反理性话语思潮进行了反戈一击。
借助文学释义证明理论自身
何谓强制阐释?张江认为,一种文学解读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从既定的理论或假说出发,强行规整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指涉,从而达到澄清理论自身的目的(《当代文论重建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就性质而言,强制阐释既不致力于文学理论的建构,也不关注文学作品的意义所指,而是强行借助于文学释义去证明理论自身。海德格尔就明确表示:“生存论分析便持驻地具有一种强行施暴的性质。”(《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由此他对《安提戈涅》的阐释就不在于文学释义,而是致力于“天命消息”的获取,企图将“不再形诸文字但却被说到了的那些含义展示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需要行使强力”(《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至于为何必须“施暴”,海德格尔说:“这种阐释若不从某种‘设为前提的’一般生存论的观念又从何处得到其指导线索呢?”(《存在与时间》)可见,理论先行是强制阐释的根源。
伽达默尔迷恋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在文学阐释上“不是把文学当做对象来进行主题研究”,而“仅仅是服务于诠释学的实施”(《美学与诗学·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解释学为何偏偏喜欢文学和艺术?伽达默尔认为:“艺术的经验……使理解的本质问题获得了恰当的尺度。”(《〈美的现实性〉中译本前言》,《外国美学》第七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换言之,理解就是文学和艺术的基本存在方式,它能够规范理解主体那些违反生存论分析指向的冲动。德里达也承认,他分析文学的目的是展开解构的思想(《书写与差异·访谈代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乔伊斯之所以令德里达着迷,就在于他的书写具有天然的解构主义特性。对德里达来说,“解构的阅读和书写不是去唤醒某种先决的、本原的意义”,而是“创造意义”,任何解构性作品的意义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和模糊的(张宁《雅克·德里达的中国之行》,《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6期)。因此,乔伊斯就是解构的幽灵,随时浮现在德里达的脑海中。在这样的视野中,乔伊斯的书写就失去了都柏林色彩,只剩语言的能指漫无边际地飘浮。
另一个强制阐释的典型是精神分析批评。弗洛伊德的《哈姆雷特》阐释并不关心文本的戏剧性和文学性,而是在乎哈姆雷特的精神分析对象性质。厄内斯特·琼斯的阐释进一步认为,克劳狄斯取代了父亲,哈姆雷特之所以犹豫,乃是因为不能容忍集乱伦与弑父于一身的念头。这些讨论引起了拉康的不满,他认为《哈姆雷特》阐明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菲勒斯匮乏引发的欲望主体”的故事。这依然是以精神分析理论假设为前提的,目的在于论述象征系统对于人的欲望能指的压抑。
不仅存在主义、新解释学、解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存在严重的强制阐释,而且以建构文学理论为旨归的理论流派也存在强制阐释的情况。如形式主义学派的什克洛夫斯基,他强调文学语言的结构和陌生化,否定文学的形象思维,声称“已制成之物”并不重要,读者不是辨识某种形象,而是体验新奇,因而建议作家要像托尔斯泰那样利用“奇特的再现”手法展示事物(《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他分析《霍尔斯托麦尔》的陌生化手法,认为事物是“通过马的认识而变得奇异化的”,人们体验的正是这种奇异之美。形式主义将语言学与符号学奉为佳臬,结果导致文学释义的澄清程度远远小于理论自身的证明。其他如结构主义、新批评、接受美学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强制阐释的情形。
就以上而言,强制阐释已经不是过度诠释与否的问题,而是根本无关于文本意义的指涉性。尽管文本的意义是多重的、复杂的,但我们能明确,有些意义并非属于文本。强制阐释而来的意义似是而非,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征用文学证明自身,背离文本原生话语的意义指涉,这是强制阐释的核心性质,势必会侵蚀、破坏文学理论的本体,使之变得越来越不纯粹,当代文论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强制阐释背逆文学规范
从批评策略看,强制阐释的首要特征是理论的机械套用,即提取作品中的某一文学形象或情节,强行套用有待证明的理论假设,以得出符合理论旨归的结论。比如拉康对《窃信案》的解析,首先将窃信情节简化为两个三角结构,“原初场景”中的三角顶点是国王、王后和大臣,“重复场景”的三角顶点是警察局长、大臣和杜宾。拉康声言,若要把握某个个体的无意识,就需要把握自我与象征秩序的关系结构:“不同的对话本身在它们对言语力量的相反运用中,具有制造不同戏剧情节张力的效果。”拉康的结论是能指性的象征秩序总是通过强制性重复来压制个体。如果不是精神分析理论在先,如果不是拉康娴熟的简化技巧,哪一种读者会读出这个意义来?
第二种策略是解构、破坏作品的原生话语,把原生文本诸要素分割,阻止文本诸要素相互作用和生成意义,破坏原生文本的意义表达机制,从而消解了意义回归文本诸要素的整体性和总体性。在《S/Z》中,罗兰·巴特将巴尔扎克《萨拉辛》分为561个碎片和五个信码,阻止“它们形成一个单一的题意集群”,使之变为非连续的、异质的意义碎片(《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巴特随意颠倒文本要素,破坏文本的意指过程,强行压制文本释义的表达,目的就是解构。
第三种策略是重置作品的元素以获取“新意”。强制阐释为了澄清理论而有意分割或删除原生文本诸要素,将之改写、重置为再生文本。重置的差异性文本与原生文本貌合神离,无法与原生文本重合。拉康和巴特的文本解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再看看赛义德对简·奥斯汀《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阐述。赛义德单单提取了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运转背景,就得出了这是一部传达帝国主义经验的小说的结论。他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是靠托马斯爵士的加勒比甘蔗种植园来维持的。原生文本的各种要素都被悬置起来,唯独放大庄园的背景要素,直接破坏了原生文本的意义表达。要知道,这是一部典型的披着爱情故事外衣的讽刺小说:通过芬妮的参照系,作品讥讽了富有的资产阶级在道德和良知方面的贫困。作品与帝国主义经验传达有何关系?但赛义德的分析还是以重置性的策略,达到了澄清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目的。
这些阐释策略直接破坏了文本的意义表达机制,消解了作品的意指性,乃至作品本身。因此,强制阐释总是背离文本的意义指涉,以非法性的强制背逆了文学阐释的基本规范。就背景而言,这种破坏、解构和重置的冲动无疑与当代西方的反启蒙、反理性、反中心的虚无主义思潮有关,各种理论话语以僭越固有边界为能事,彰显所谓文化政治的姿态。
强制阐释不是过度诠释
由于在背离文本意义指涉方面的相似性,强制阐释容易被误解为过度诠释。事实上,二者有着根本区分。艾柯的过度诠释针对的是“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力”(《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些阐释者完全不顾及作者赋予文本的意义,而是带着自我经验或者理论视角,假借文学释义的名义捕捉那些“神秘莫测”的本质。这与赫施的阐释立场基本一致,都将诠释的过度性放到了僭越作者层面的文本意义上,这是过度诠释的核心所指。从这个角度看,过度诠释与强制阐释并非泾渭分明。然而关键在于,强制阐释不仅偏离了“作者意义”,而且偏离了文本诸要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意义;过度诠释尽管天马行空,但依然在阐释文本,坚持从文本出发的路径,而强制阐释的路径是倒置的——先从既定的理论出发,如同霍夫曼-阿克斯特黑尔姆指出的,“理论和艺术变成了空洞的概念”(《先锋派理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由于强制阐释与过度诠释的内涵不同,对二者的反思批判的目的也不同。过度诠释批判针对的是“读者冲动”和阅读的有效性,而强制阐释批判则指向文学阐释的僭越性和非法性,更确切地说,强制阐释批判提出了当代文论危机根源的问题。对过度诠释的反思尽管反对理论的强制,但对场外理论还抱有幻想。比格尔就认为,“将过去寄予希望的思想碎片通通扔掉”标志着左翼知识分子的危机感,因而有必要“将反思性地运用一部作品与对它的释义区分开来”,运用作品的活动“需要标准,只有理论才能提供这种标准”(《先锋派理论》)。
比格尔并未看到理论强制介入文学阐释的后果。艾柯也没有看到,理论至多只是通过文艺阐释填充自身的空洞性或矫正自身的片面性,当代西方文论危机的根源正是一些非法寄生在文学身上的理论造成的。它们依赖文学艺术的阐释来繁衍自身,结果不仅会破坏文学阐释活动,而且也会消解理论自身。伊格尔顿曾慨叹:“理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对此,我们是应该沉思,还是该发出惋惜的哀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