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孙卫国 郭江龙
【核心提示】实录作为体例严谨且编纂有序的史书,在史料流向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当朝国史、异代纪传体正史、编年体史书等其他史书的上游史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史专题研究日益深化,其中武汉大学谢贵安教授对于中国古代实录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他在博士论文《明实录研究》和专著《中国实录史学研究》基础上完成“实录研究书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套书包括《中国已佚实录研究》、《宋实录研究》、《明实录研究》和《清实录研究》4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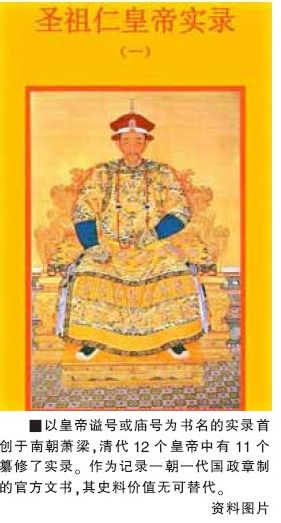
实录体元、清两朝不设附传
作者对实录体1400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整体观察,在理论上对实录体史学进行分析和概括,明确提出“实录体史学”的概念,并根据南宋王应麟所云实录“杂取编年纪传之法”的说法,指出实录是介于编年与纪传之间,以“编年附传”为特点的史书体裁。即融合编年体与纪传体的特点,以编年顺序为叙事线索,在人物去世或赠官之时插入附传。书中还指出,实录体到了元、清两朝均不设附传,从而沦为纯粹的编年体,这表明实录体作为一种独立体裁亦有脆弱性特点。该书还从政治鉴戒、道德劝惩、教育考试和学术考证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古代实录的价值与功能,进一步肯定了在纪事本末体产生以前,实录体、编年体和纪传体构成中国古代史体三大支柱。
综观“实录研究书系”,所引史料广博而翔实,条理分明有序。以《清实录研究》为例,作者将实录研究建立在档案史料基础上,对《世宗皇帝上谕档》、《乾隆朝上谕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等清代档案进行细致梳理与考订。在此基础上,参考“清三通”、《大清会典》、《清国史》、《清史列传》、《清史稿》、清人文集、清代日记等史料,对于《清实录》各方面的问题进行逐一探讨。与此同时,还将记载同一史实的史料,按档案、实录和其他史籍的分类顺序加以排比和征引,缕清史料流程并分别史料等级,使卷帙浩繁的史料变得条分缕析,应用有序。
宋代实录独立成类
实录体史学的研究专著,仅有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一部。该套书的出版,有助于推进中国实录研究系统化。以《宋实录》研究为例,学界对于《宋实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等,其他实录特别是南宋实录研究,多付阙如,谢贵安的《宋实录研究》弥补了宋代实录研究中的薄弱环节。
“实录研究书系”既有宏观探讨和整体观照,也有个案研究和微观考证。如在《中国已佚实录研究》中,作者从目录学角度,通过《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志目录的分类,对实录地位的升沉进行解析,从而进一步探讨实录性质的变化。在具体的历史考订方面,作者将《宋实录》所附传记与现存《唐顺宗实录》进行对比,发现宋人杜大珪摘抄出来编入《名臣碑传琬琰之集》的27个人物传记篇幅均较长,最长的为韩维传记,多达4409字,最短的章惇传记也有542字,平均字数为1876字,远远超过《唐顺宗实录》的630字。以此证明实录作为“编年附传”体裁的特色,以及在宋代目录著作中独立成类的原因。
《清实录》存在汉化现象
该书系还运用社会史方法,对实录的纂修与少数民族汉化问题进行研究,如《清实录研究》中,对实录这种史书形式在清王朝“汉化”和“专制化”过程中的适应和影响作了分析,发现《清实录》无论在纂修观念、制度、体例,乃至秘藏制度上均仿行汉族政权所制定的实录体式。如作者所言,“随着汉化的不断加深,《清实录》在正统观念、尊君意识和史书形式三个方面皆出现汉化现象。如用干支代替数字记时,用文言代替粗浅的语言,用标准的汉译名词代替随意译成的粗鄙名词”,反映出多民族国家政治一统和文化融合的趋势。
作者将实录的史料来源加以分类,分为原始档案(包括诏令敕书、公文奏牍等)、初级史料(包括起居注、时政记)、二级史料(日历)和其他史料(包括笔记、小说、文集等),同时指出实录作为体例严谨且编纂有序的史书,在史料流向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当朝国史、异代纪传体正史、编年体史书等其他史书的上游史源。
《清实录》对清代历史影响深远
作者以《皇朝通志》编次手法为切入点,认为《清实录》去掉附传的原因,与清人注重史学体裁的功能区分有关。另外,元代《元实录》与《后妃功臣列传》分途而修的做法,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实录》的体裁特点。同时,作者以动态研究思维辨析《清实录》的史料价值。清代《满文老档》、《旧满洲档》、《上谕档》等原始史料尚有见存,就其史料的原始性而言,远胜于《清实录》,但是从传播学和阅读史角度来看,《清实录》具有查阅性更强,对清代历史的影响较上述档案既早且远的优势。同时,作者从《清实录》对于清代历史的记载之功,对其他文献的考证之功,满文、蒙文《清实录》的特殊价值以及《清实录》在现代的整理与应用等方面进行论证,肯定了《清实录》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以一人之力成就四部专著,难免存在不足。大体而言,全书“述”的成份较多,“论”的成份稍显不足,史料有堆砌之嫌;书系中亦存在一些校刊不精的问题,如《清实录研究》第488页“仁宗在主导的《世宗实录》中”,“仁宗”应改为“高宗”。某些论断可以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如《清实录研究》中,将《清实录》追求原始档案、记注文献的史学传统和兰克学派重视“一手史料”的学术理念进行对比时,未能作充分引申和阐述。书中涉及东西方史学比较的理论分析,也有待进一步加深。笔者曾撰《〈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像这类将中国实录与东亚诸国实录的比较研究,该书系尚有待开发。